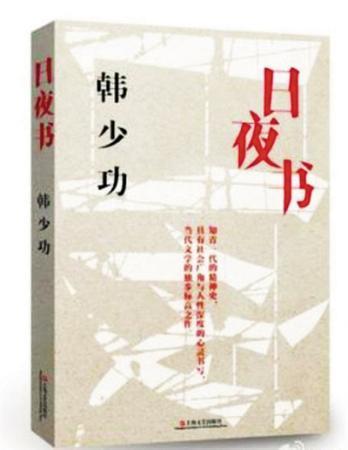

作家韩少功近日推出新作长篇小说《日夜书》,这是他继《马桥词典》、《暗示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。这本描写知青群像的小说,描绘知青一代的心灵史和精神史,重点关注他们在当下的命运。
从《爸爸爸》到《日夜书》,韩少功的创作速度并不快,但每部作品问世总能引发人们热议。而另一方面,他也曾身兼数职,参与行政工作。2000年,韩少功辞去《天涯》社长及海南省作协主席等职务,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湖南乡下。2011年,他未到退休年龄坚持“裸退”,又放弃了海南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位。
韩少功说话温文和蔼,但言简意赅。电话一打就接,但是对于他自己觉得过于重复、自我宣传的题目,一个都不答。他如今已年至花甲,笑说自己正在“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”。
壹
“老马”在中国的影响似乎被说过了头
羊城晚报:从《爸爸爸》到《马桥词典》到《日夜书》,您的小说叙事方式一直在改变,在文体创新上,您是否有预想的一个写作脉络?
韩少功:没有,完全没有。写作受制于各种条件,而这些条件是不断变化的,比如我只有面粉的时候就吃饼,只有大米的时候就喝粥,如果饼和粥都吃腻 了,条件许可的话,我就试一下做法国大菜。哪一种小说样式最合适我,不是一个理论问题,是一个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,得慢慢地试,得相机行事。
羊城晚报:这么多年过去,现在回头看《爸爸爸》,您是否会认为当年这部小说的技巧性过重了?您现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?
韩少功:我很高兴自己有过《爸爸爸》这样的技术训练。好像是王安忆说过:一个作家毕生的写作就是造一个房子,里面有柱子,有梁,有墙,有门……《爸爸爸》有点寓言化,是这个房子里的某一扇门和某一个窗,不一定好,但不是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的。
羊城晚报:《日夜书》中有多个句子类似于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。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作家,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加西亚·马尔克斯,或者说是拉美文学的影响?
韩少功:不是那样吧?老马的那种造句,是把三个时态压缩在同一个句子,我想学也学不来。我只是用了一般的倒述句,很普通的。我当然喜欢这位拉美 作家,受了他多大的影响,自己也不知道。但他在中国的影响似乎被一些人说过头了,比如有一位国外的汉学家,以为中国文学里从来没有神话,作家的夸张变形都 是从拉美学的。我说你读一读《山海经》或《搜神记》再说吧。我那篇《归去来》,明明是庄周梦蝶的结构,但有人也用来联系老马,实在没办法。
贰
不想把知青题材写成“表功会”或“诉苦会”
羊城晚报:《日夜书》与其说是写那段知青历史,不如说在言说当下。谁都逃不出历史的阴影,谁都要面对幽微的人性。几十年前一样,今天亦然。而这种历史与现实交叉的叙事方式,是您有意为之的介入现实的方式?
韩少功: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:“一切历史都是现在时。”哪怕说汉朝、唐朝、明朝那些事,也都是古为今用,是旧事新说,何况我写的历史近在昨天,何况这本书里至少有一半的内容就是说当下。很多事物既要近距离看,也要远距离看,这样才能看得更透彻。因此历史与现实交叉的方式,是我表达这个题材所需要的。
羊城晚报:你为什么要写这一个知青群体的群像?就像一篇评论说的,写一些“令人屏息的兵马俑”?
韩少功:我不想把知青题材写成“表功会”,也不写成“诉苦会”,只是想写一些有弱点的打拼者甚至英雄。比如姚大甲一生沉迷艺术,但有点太玩世吧?小安子决不妥协地追求浪漫人生,但有点脱离现实过于小资吧?马涛是启蒙精英,但毛病是自恋和自大。贺亦民以野路子的技术报国,但遭到官僚主义、旧体制的打击,最后入狱也有自己性格过于粗放的原因。陶小布貌似最成功,其实连抵制一个小小的贪腐也上下无援,员工们反大腐,自己却也小腐,最后在公车改革一事上把他打入困境。至于郭大军,忠厚哥,进入新时代后处境灰暗,最容易怀旧。妻子出走是他“文革”中那点政治优势失去后的历史还账,“问题女儿”则是来自消费主义的压迫……总之,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光环偶像,却是我心目中英雄的日常版,是普通人的悲苦和抗争。
羊城晚报:你在追究历史原因,比方说反思“文革”与市场化的时候,好像反对把一切责任推给社会和时代,倒是把放大镜对准人物之间性格、心理、人性的差异,甚至毫不掩盖受害者的浅、伪以及荒唐。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几乎从未看到。
韩少功:指责他人是很容易的,抱怨时代也是很容易的,但这样做不会给自己真正加分。相反,一代人不再自恋,敢拿自己开涮,敢给自己找毛病,才是在精神上的成熟与强大。如果很多前人没做到这一点,那么这一代应该做到。在这一点上,自我反思其实是给这一代人再加分的机会,一次迟到的机会。
叁
根据自身所长来选择介入现实的方式
羊城晚报:您认为作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现实呢?
韩少功:情况不大一样。有些人写报告文学,比较接近新闻,与现实的关系有点像短兵相接。有的人写神话,写史传,写田园诗,写儿童文学,就有点长效养生的味道,不能像速效药那么立竿见影。再说“现实”也是一个容易误解的概念。反腐是现实,恋爱也是现实吧?改革是现实,在月光下幻想一下外星人也是现实吧?沈从文当年写《边城》,没去写打仗和游行,有人说他是脱离现实。但中国如果没有《边城》,恐怕也是有点遗憾的。作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所长来选择介入现实的方式,速效药,长效药,都可以。相反,如果制定出一种所有作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方式,倒可能把事情搞砸。
羊城晚报:除了小说,您也写散文,《山南水北》得到众多褒赏。《日夜书》是否含有打破散文和小说的界限的意图?
韩少功:《马桥词典》、《暗示》、《山南水北》以及这本《日夜书》,都是我结合小说与散文的尝试,只是各种元素的配比不大一样。其实历史上的体裁一直是流动的,变化的,也是开放的。奈保尔的代表作《抵达之谜》就更像散文,没什么情节。我的《日夜书》里情节不算少,但我有意留下一些回忆录的笔法,留下一些毛边、不对称、跳跃性的空白,使它更接近生活和回忆的原貌。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有些起承转合得十分标准和严格的小说,自己也会写一些。作家有不同的选择,在不同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选择。
羊城晚报:金雁的《倒转红轮》获得今年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,但作者本人也纳闷,为何《倒转红轮》这种历史研究专著会被纳入散文范畴。您认为散文这种文体是否有边界?
韩少功:丘吉尔是个政治家、演说家,却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庄子的理论文章,也可以当散文看。在俄国文学传统里,根本就没有什么“小说”,无韵的叙事统统叫散文。我们不妨把散文当做一种弹性最大的文体。
肆
作家应该坐到自己的书桌前“抗晕”
羊城晚报:在文学创作之外,您曾经的一系列迁移、辞职、“裸退”等行为也颇引人注目。为什么这么做?
韩少功:有一些投身公共事务的经历,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我不擅长行政,把自己觉得该办和能办的事办完了,再待下去就是混事了,当然应该下台走人。下台的那天,我读完换届报告就把房钥匙和车钥匙交了。别人问我啥心情,我说“翻身农奴得解放”,哈哈。
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,但定力方面可以打高分,该干什么就干什么,对忽悠有免疫力。我阶段性地住乡下,可以靠近自然和底层,还可以屏蔽掉一些有害信息和不良关系,相当于给自己赚回来一些时间与生命。有什么不好?眼下不仅国人浮躁,好像全世界都浮躁。信息爆炸造成了第一晕,恶性竞争造成了第二晕,城市太大造成第三晕……一个作家应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,有一点抗晕的本领。
羊城晚报:您给人感觉是敦厚随和的,但在您的内心,对人对事对文学,定有自己的一套准绳与思考。当二者出现某些冲突时,您会不会感觉痛苦?
韩少功:我这个人四十岁以前有一些脆弱,还是年轻人嘛。一是关于结果:有时候明明自己费力了,但结果不好,令人灰心。二是关于团队: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者,后来发现不是,于是觉得自己很受伤。现在的我可能有点没心没肺,叫做“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”,不再那么看重得失,不再那么看重亲疏,所以就不容易受伤了,没什么好事也可以傻乐。比如写出一本书,只要写作过程很开心,有创造的快感,别人怎么看都可以忽略不计。
链接
韩少功,1953年出生于湖南。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曾是倡导“寻根文学”的主将。曾担任海南省文联主席。2002年4月,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“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”。代表作有: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《暗示》《日夜书》,中篇小说集《爸爸爸》,散文集《山南水北》等。作品有三十多种译本在境外出版。
